对于电影空间性的研究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艾森斯坦时期,人们通过建筑本体在电影中的呈现来研究虚拟空间对于物理空间的参照与再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空间影像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电影人开始关注空间认知的同构性。
作为传统建筑一种重要的元素载体——古典园林,其与电影在叙事模式和视觉传达上都具备同构关系。
电影学者朱莉安娜曾经基于对现象学的研究提出“如画园林”的理念,这和古典园林建造家们追求的“景在眼前”和“步移景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艺术氛围的沉浸体验
与通过用光、透光追求“立体感”的西方绘画不同,中国画的表达以“去光性”和“无几何比例”为主,大多通过写意的笔法来制造氛围。
园林艺术对绘画进行了继承发展,力图让观者得到氛围的包裹,取得“人在画中游”的沉浸体验。

中国电影与这些艺术模式一脉相承,《香雪海》的导演费穆就曾在《略谈“空气”》一文里指出“氛围是电影的内在气质”,“氛围是一种过于整体的映像”。
台湾的侯孝贤便是营造电影氛围的高手,他的早期作品大多使用柔和的自然光,对光线的层次性进行弱化,使得道具布景都能保持原本的质地。
在《刺客聂隐娘》中,他通过雾气与自然光的交映,使画面的“空气感”进一步加强。
电影与园林对于艺术精神的延伸高度类似,都试图打造让观者“身临其境”的具象图像,电影可以利用视觉变化增加观者的感受,通过对画面的感情投射引发审美体验91秦先生。
(二)电影的空间叙事
不同的艺术模式在空间经营上会采取不同的手法。古典园林主要通过种树,设水,叠山等手法来打造空间的意境感。
《园冶》一书中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来形容园林对天地之景的呈现。
而电影则着重于对虚拟空间的塑造,电影当中所构建的影像时空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现象的投射。
电影需要通过具体的空间环境来开展影像叙事,各类人物的运动都在这个空间环境中被产生和接纳。
镜头是影片叙事的技术手段,作为趋势空间的搭载,无论是运动镜头还是静止镜头,都能够对系列空间的不同形态进行展现。
虽然景况会对荧幕画面进行限制,但在景况之外,电影能够延伸出更多暗含的隐性空间。
利用不同镜头的剪辑与组接电影,能够为观众塑造一个变换的空间,即使采用实拍场景剪辑而成的空间也未必真实。
《师父》一片中,在胡同里有一场较为激烈的打斗戏,但实际的拍摄场景只有一堵墙。
电影学者库里肖夫提出,把不同地点的素材放到一起进行剪辑,能够打造出虚拟的影像空间,他将其称作“人造景观”。
(三)空间的叙事推动
利用精心组织的镜头内容,电影能够对空间与时间进行塑造,进而推动情节叙事。
电影人物的情况都是固定的,因此构图设计对于影片的效果呈现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古典园林中有借景手段,能够对单一视域里的各类信息元素进行延展,电影的构图方式也采用了这种手法。
在运动中进行构图设计,除了要对镜头内容进行精心的安排组织,还要通过前后颈之间的交换配置来对人物关系进行丰富的展现。
侯孝贤经常使用的固定长镜头和小津安二郎经常使用的景深镜头,都是电影在展现人物关系时较为常用的方法。
抑景、夹景、框景等中国古典园林当中的造景手法,都是通过在主要景观面前设计前置景观来对观者的视线进行引导。
例如苏州的沧浪亭,园内群山环绕,园外水波粼粼,四周回廊幽静,花香以闻,墙上的漏窗投映出园外的景致,最能吸引游人的注目。
心理学的研究曾经表明,人类普遍具有窥视的天性,封闭性和指导性的空间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窥视欲。
漏景和框景的拍摄手法使这种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使得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取得更好的交融效果。
《刺客聂隐娘》中,经常采用前景遮挡来进行画面构图,漏窗、帷幕等物件。
在物理空间上将田季安与聂隐娘进行了隔离,也使观众身临其境地理解聂隐娘的视角,在宅邸之中从“局外人”的角度对其他人的一举一动进行窥视。
《我不是潘金莲》则用圆形画幅来充斥全片,给观者一种窥探秘事的感觉,又颇具园林趣味。
(一)观者视角的变化
电影和园林这两种艺术都以调动观者的感知作为目的,把人作为最为重要的元素,希望让观者能够参与其中。
作为整体空间的一部分,人也是环境当中的重要构成,《说园》所描绘的园林最高境界便是“园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与景和,景因人异”。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既能对空间起到装点,又能够对空间进行重构。在“看与被看”的交替轮转中,完成主动和被动的交替沉浸。
观者在园林之中漫步欣赏,通过步伐和视线的移动来对外部图像进行捕捉,这种模式可以与电影中的镜头画格、故事脚本进行类比。
这种模式在电影中是奠定审美基调的重要一环,也对观者的感官定位进行了明确。
园中漫步是通过观者的眼睛寻找景色,而电影拍摄是通过摄像机的视角去建构空间。
通过在园林空间里产生的相对移动,观者能够对观看视点进行选择,电影则会在特定时刻通过摄影机的移动来凸显特定的角色背景,从而进一步加深观众对于角色的理解认同。
在《青木瓜之味》一片中,导演陈英雄打造出了一个富含古典韵味的园林空间,利用对前景的虚化和长镜头的运动,让观众带入到旁观者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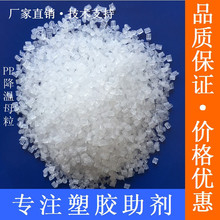
前半部分的故事情节基本上都在这处宅院里发生,梅从起初的外来者,逐渐变成了一名.融入者。
在外来者阶段,梅只在这个家庭当中作为一名功能性成员而存在,所以长镜头的画面很少将梅作为主体去呈现。
而在后期,梅对于家庭的融入逐渐加深,开始在家庭中发挥情感作用,因此长镜头开始将梅作为主体去进行表达。
尽管处在同样的空间里,但当角色的定位出现潜移默化的改变时,观众的视点也随之更改,宅院空间也被逐渐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性含义。
(二)体验过程的变化
艾森斯坦曾经将雅典城比作是“一个古老的电影”,他形容雅典城具有“最完美的镜头长度和镜头设计”。
对于影像和景观的观赏本质上都是一种体验,利用运动来对空间进行更多的感知。
因此观赏电影与观赏园林一样,都是借助观者在空间里产生的相对运动来实现的,欣赏园林的方式能够在电影中得到轻而易举的应用。
在影片《枯木逢春》里,负责美术设计的人员刻意地提高方东哥房子的高度,而拉低苦妹子家的高度。
方东哥房子建造在高坡上,而苦妹子的房子在竹林的平地里。这种空间设计能够让运动镜头“步步入胜”的效果更加明显。
欣赏园林时,观者通常采用一种“漫游式”的视野变换,从后至前,从远景到近景,观者的视点可以随心情任意调换。
这种观看方式清晰地呈现出了运动、空间与叙事的关联,能够给电影的空间叙事模式提供借鉴91秦先生。
电影创作需要站在观者的视角对画面进行模拟,利用镜头中的蒙太奇或者单纯的蒙太奇手法,可以对空间视点进行选择性构建。
摄像机的眼睛具有比人眼更为复杂的技巧,通过摄像机,电影能够对单一的画面进行不同效果的呈现。
根据叙事情节的推进,摄影的角度可以随之调整,光线的强弱也能够依照角色情绪的变化而变换。
“园日涉以成趣”的这种趣味体现在欣赏的节奏和视点上,中国电影的拍摄手法也自觉继承了这种审美。
上世纪的《野玫瑰》、《早春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都纷纷使用了移动摄影的手法,在影片中打造了移动映影的空间画面。
镜头采用不疾不徐的节奏进行拍摄,仿佛人总行走在园林中的步伐,通过运动镜头动态地展现了电影的叙事空间。
当我们对一个空间进行描述的时候,仅凭理性描述无法对其空间形态进行确定,只有把叙事和空间进行连接,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
因此作为同一现象的两面,空间和叙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古典园林在对空间进行建构的时候,力图在有限的时空里融入无限的时空,中国电影对古代的造园术有着精神层面和艺术层面的继承。
在造园中,“借景”的手法占有重要地位。
历数我国有名的古典园林,无不使用了借景的方法来营造景观。
园林借景利用楼阁和墙院来对空间进行分隔,又通过漏窗洞门和花草树木对空间进行联系,使得景观空间具有隔而不绝的效果,宛如天成佳作。
这一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类似于巴赞电影学说当中的景深镜头。
在电影语言发展史中,景深镜头的应用是具有辩证意义的一大飞跃,在增强电影空间感的同时,也扩大了荧幕空间所包含的内容。
和西方惯常使用的透视光影不同,东方在空间感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多以散点透视为主,但这并不能够帮助电影营造空间感。
因此动画电影经常借助园林和绘画当中的借景技术来表现空间感。
《三峡好人》这部影片主要以刻画特殊环境里三峡移民的困难生活为主,对于空间和人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在韩三明将要离开三峡的场景中,采用了中景和固定长镜头,画面远处在两栋大楼之间悬挂着一根钢丝,有一个人在上面走着。
就这两个镜头放到一起,并不是单纯的描绘真实的画面,而是透过这种场景去传递一种想象和隐喻。
而韩三明与前妻回到拆迁楼的那个镜头,采用的是中远景。在一片断壁残垣中望出去,能够看到被拆得四分五裂的三峡。
二人坐在这安静的角落里,重新和好,墙外的大厦在这相对无言的安静时刻忽然倒塌,观众顺着两人的视线一起向外看去,这堵墙把外面的世界和韩三明进行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阻隔。
韩三明能够在墙内安静的遥望大厦的崩塌,仿佛墙内的他们与这一切毫无关系。
《三峡好人》对借景技术的实践应用不仅仅停留于人造景观。
园林的借景会受到物理空间的客观束缚,但电影不同。它能够在借去自然景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会和心理景观进行借取。
只要符合情节叙事的推进,任何发生在电影场景中的借景都是合理的。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也是营造园林景观的一大特点。想要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呈现出更大的天地,就必须对已有的自然元素进行符号性的转换。
电影也经常进行符号转换,利用蒙太奇的手法把时空的巨大流转缩小近短短的几个镜头当中。
电影《海上花》就把“长三公寓”这一故事发生地作为一个符号,通过对这个符号的细致描写,来达到虚化整个时代的目的。
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能够使观者利用认知去填补空白,将零散的信息片段进行连接,从而更大程度的丰富影像的意义。
91秦先生 91秦先生


